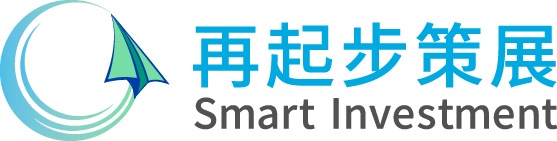在接近叢林法則的政治現實中,為何仍要保留道德不安
有一段時間,做記者的時代,在大學的時候我是主修數學副修哲學,開始做記者的時候還真的很天真爛漫,遇到很多制度不公的時候,我以為自己的不安來自資訊不足。只要多讀一點條文、多理解一點制度設計、多分辨一次合法與非法,心裡的那個結就會解開。
後來才慢慢明白,那不是知識的問題。
而是一個更難承受的事實——制度本身,在運作的時候,往往都會失去它曾經承諾過的道德重量。
當政治越來越接近叢林法則,當結果一次又一次被用來合理化動機,當「成功」開始取代「正當」成為評價的核心,我們真正面對的,其實不是國際局勢,而是自身價值的安放問題。
如果這個現實令到大家心理不安,雖然這樣說很奇怪,應該值得慶幸的。

⸻
一、制度為何曾經讓人安心?
制度之所以重要,從來不只是因為它有效率。
而是因為它承諾了一件事:
世界不完全由強者決定,
行動必須先通過某些原則的審查。
這個承諾,讓人願意忍受暫時的挫敗,
也讓弱者能相信「不公平不等於合理」。
在哲學上,這種直覺最清楚地體現在
Immanuel Kant (康德)的倫理觀裡——行動是否正當,取決於它是否符合可被普遍化的原則,而非結果。
即使你輸了,至少你沒有違反你所相信的規則。
制度的安慰,正在於此。制度應該帶給我們保障,至少可以提供安慰。
⸻
二、但政治從來不保證這個承諾會被兌現
真正讓人不安的,不是世界變得殘酷。
而是我們突然意識到:世界其實一直如此,只是我們曾被制度暫時保護。
在國際政治、戰爭、權力競逐的現實中,結果不只是後果,它往往反過來定義了什麼叫合理、什麼叫必要。
這正是功利主義者John Stuart Mill (穆勒)所能平靜接受的世界:如果總體後果更好,那違反原則便不再那麼不可原諒。
政治現實一次又一次告訴我們——制度不是裁判,制度是勝利者整理完局面後才補寫的說明書。
這不是陰謀論,或者事後孔明,而是歷史常態。
⸻
三、不安其實來自一個更私人的問題
真正讓人難受的,往往不是「世界變壞」,而是這個問題:
如果結果真的可以洗白一切,
那我們曾經學習及堅持的原則,是否只是天真?
當我們發現:
• 違規者沒有被懲罰
• 成功者被重新定義為「英明」
• 公義變成一種事後修辭
不安便不只是政治性的,而是存在性的。
我們開始懷疑:是不是只有輸家,才需要談原則?才會被原則要求,才會被要求遵守原則。
⸻
四、德性倫理提供了一條不同的出路
如果義務論太脆弱,結果論又太冷酷,那是否還有第三條路?
古希臘哲學家Aristotle (亞里士多德)提供了一個至今仍然有力的視角。
他不先問「規則」或「總體結果」,而是問:
在這樣的情境下,一個成熟的人,應該成為怎樣的人?
德性倫理的重點,不在於控制世界,而在於不讓世界完全重塑你。
你也許無法阻止權力用結果合理化自己,但你仍然可以決定:
• 自己是否接受這種語言
• 是否在理解現實時,仍保留道德張力
• 是否拒絕把「成功」當成唯一的價值尺度
⸻
五、安頓不安,本身不是軟弱
在接近叢林法則的現實中,不安其實是一種道德警覺,而不是缺陷。
真正危險的,不是對制度公義失去信心,而是對這種失去完全無感。
當一個人再也不為「是否正當」感到困擾,只剩下「是否有效」,那他其實已經被現實徹底收編。
安頓不安,不是說服自己接受一切,
而是學會這樣生活:
我知道世界未必公義,
但我仍然選擇不把這件事合理化到毫無痛感。
⸻
六、一種成熟的自處方式
或許,真正可行的姿態是這樣的:
• 在分析上,承認結果確實塑造秩序
• 在理解上,不再幻想制度必然正義
• 但在價值上,拒絕讓「結果」成為唯一語言
你可以看懂政治的殘酷,
卻不必把它內化為自己的倫理。
⸻
結語|為何我們仍需要保留這份不安
也許,制度的公義真的正在退場。
也許,世界正在重新學習如何以力量說話。
但正因如此,
個人的倫理感,反而變得更重要,而不是更過時。
因為在一個只問「誰贏了」的世界裡,
仍然願意問「這樣對嗎?」的人,
不是幼稚,而是在替未來保留一條尚未被封死的路。
不安,並不是因為你看不清現實。
恰恰相反,它是你仍然沒有放棄成為一個負責任的人。
後記:這篇文章的緣起是我有一個很私密的群,都是留在香港、更多是流散在各地的朋友,某程度上都是志同道合,但昨天因為委內瑞拉的事件,罕見地有不同的意見在交流。
文章寫得再多,自己很明白,有時候不是替世界找答案,而是替「還在意對錯的人」找一個站得住的位置。
這些書名標籤,不是裝飾,而是告訴我們:
我們並不是孤單地感到不安,這份不安,本身有一整條思想傳統在支撐。
吾道不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