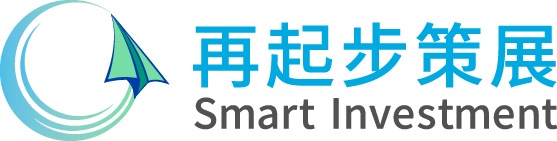由達沃斯論壇到和平委員會:
特朗普正在走向自我孤立?
今次特朗普,宣佈自己滿載而歸。
特朗普出席了瑞士達沃斯(Davos)的世界經濟論壇(World Economic Forum, WEF)。
格陵蘭問題暫時降溫,因關稅引發的緊張氣氛被刻意淡化;他在論壇期間高調宣布成立「和平委員會(Board of Peace)」,並在社交媒體上形容此行「滿載而歸」。
真的如此嗎?
如果只看表面,答案似乎是肯定的。
特朗普在達沃斯宣布成立和平委員會,宣稱加薩戰爭「真的正在走向終結」;
在抵達前,他已取消因格陵蘭問題而引發的關稅戰,成功把議題從關稅、盟友分歧與歐洲不滿,轉移到「和平倡議」與「全球穩定」;
他也一如以往,在公開場合點名批評盟友的國防支出,重新把話語主導權握回自己手中。
從政治表演的角度看,這是一場熟悉而流暢的操作。
所有事情,看起來都按照他的節奏推進。
但如果把鏡頭拉遠一點,問題就變得沒那麼簡單了。
⸻
因為就在同一個時間、同一個地點——瑞士達沃斯——
歐洲主要國家領導人、加拿大、英國,以及歐盟本身,正在用另一種語言,反覆討論一個沒有被明說,卻不斷浮現的主題:
達沃斯向來不是簽約的地方,而是一個測量距離的場所。
而今年,距離感異常明顯。
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,
從達沃斯的低溫對話,到幾天後「和平委員會」的冷清場面,一條耐人尋味的對比線索逐漸成形——
特朗普看似滿載而歸,但美國,是否正在付出另一種代價?
⸻

在論壇上,比利時首相 Bart De Wever 直接點破歐洲心中最深的矛盾:
“Being a happy vassal is one thing. Being a miserable slave is another.”
「快樂的附庸是一回事,悲慘的奴隸是另一回事。」
這不是反美,而是反「被迫選邊」。
當盟友的行為變得不可預測,配合本身就會轉化為一種風險。
德國總理 Friedrich Merz 的說法,則更像一份冷靜的時代診斷:
“The world is entering a time of great power politics.”
「世界正在進入一個大國政治的時代。」
這句話真正的指向,並不是中國或俄羅斯,
而是一個更現實的判斷——聯盟不再自動存在,必須被重新經營。
⸻
這種氣氛,在歐盟執委會主席 Ursula von der Leyen 的發言中,被轉化為制度語言:
“Europe must be autonomous where necessary, and interconnected where possible.”
「歐洲必須在必要時保持自主,在可能時保持互聯。」
這句話,幾乎可以視為整個歐盟對美國態度的總結:
不是切割,而是去依賴化(de-risking, not decoupling)。
加拿大總理Mark Carney的語氣更為溫和,但界線同樣清楚:
“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works best when it is based on mutual respect, not pressure.”
「跨大西洋關係運作得最好的時候,是建立在相互尊重之上,而不是壓力之上。」
這不是外交修辭,而是一種警告——
當「壓力」成為常態,合作就不再是理所當然。
⸻
英國的立場,則顯得更加矛盾。
首相Keir Starmer在論壇上強調:
“Alliances only endure if they are predictable and trusted.”
「聯盟之所以能持續,是因為它們可預期、值得信任。」
而幾天後,英國外交大臣 Yvette Cooper 便直接表明:
“The UK will not be a signatory today.”
「英國今天不會成為(和平委員會)簽署國之一。」
理由很直接——
英國無法確定,這個由美國主導、同時邀請俄羅斯的「和平委員會」,
究竟是真正的和平機制,還是一種即興的權力安排。
⸻
場景隨後切換到 22 日的「和平委員會」簽署儀式。
特朗普在台上宣布,加薩戰爭「真的正在走向終結」,
同時點名批評西班牙:
“They want to freeload.”
「他們想搭便車。」
這句話或許能取悅部分國內選民,
但在外交語境裡,幾乎等同於向盟友公開宣告——信任已不再是前提。
結果是,美國的傳統盟友集體缺席或觀望;
德國、法國、義大利拒絕加入;
加拿大、英國選擇保持距離;
俄羅斯受邀卻未出席;
中國亦保持低調。
最終出席的,多為中東、部分中亞與東歐國家。
而白宮隨後成立的「執行董事會」,成員幾乎清一色是特朗普的小圈圈——Marco Rubio、Steve Witkoff、Jared Kushner、Tony Blair。
這讓整個「和平委員會」,看起來更像一場去制度化、去多邊化的權力實驗,而非一個能讓盟友共同承擔政治風險的框架。
⸻
把達沃斯與和平委員會放在一起看,一條清楚的線索浮現出來。
在達沃斯,歐洲、加拿大、英國談的是:如何在大國政治回歸的世界裡,保留制度、自主與選項。
在和平委員會,美國展現的卻是:願意跟上就留下,不跟就被點名。
這兩種邏輯,正在快速拉開距離。
⸻
所以問題或許不是:
特朗普是否「想令到美國被孤立」。
而是——
當美國的行為模式,迫使盟友反覆計算政治成本時,自我孤立是否已經成為一種結構性結果?
從達沃斯到和平委員會,
世界看到的,不是一個失去力量的美國,
而是一個正在失去「被自動配合」能力的美國,以往會自動配合美國方向走位的歐洲陣營不見了。
而這,可能比任何地緣政治對手的崛起,都更值得警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