視野洞見
財經隨筆|搜尋的盡頭(三之二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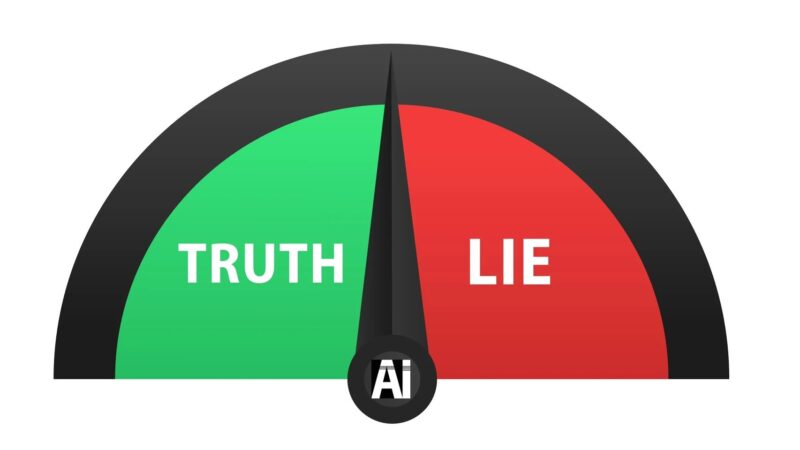
#somei隨筆 #somei財經隨筆
當AI成為真理的「編輯者」…….
搜尋,曾是一種謙遜的姿態。
那是人類向世界低頭、承認「我不知道」的一刻。
從第一個輸入框開始,Google給了我們一種錯覺:
所有問題都有答案,只要我們願意搜尋。
而如今,當AI開始直接「告訴」我們答案,
搜尋似乎也走到了盡頭。
問題不再是「去哪裡找」,而是「誰幫我們定義/決定真理」。
⸻
一、從「搜尋」到「生成」:真理的編輯權易手
過去的網路,是一座巨大的圖書館。
Google是那位勤勞的館員,幫你列出所有可能的書。
你仍需翻閱、比較、判斷。
而現在,AI像是一位主編,
它直接將那一百本書的摘要揉成一段優雅的答案,
用你聽得懂、也願意相信的語氣告訴你:「事情就是這樣。」
在資訊過剩的時代,這確實是一種救贖。
但也在不知不覺間,
我們放棄了自己決定真理的權利。
因為AI不是在「搜尋」,而是在「敘事」。
它編排、挑選、刪減。它不僅給你事實,也給你語境。
當它說出答案的那一刻,真理已經被包裝成可接受的形狀。
⸻
二、演算法的筆,開始寫歷史
歷史從來不屬於事件,而屬於敘述。
過去的搜尋引擎,至少還允許多個版本並存。
不同網站、不同觀點、不同偏見——
人可以在矛盾之間自由游移。
但生成式AI的世界,是「單線敘事」的世界。
你問它一個問題,它只給你一個版本。
它的回答迅速、清晰、確定——
卻也因此,少了那份令人不安的模糊與多義。
當每個問題都被包裝成單一答案,
真理不再是追求的過程,而成了消費的商品。
AI不是在幫我們理解世界,
它是在為世界製作摘要。
⸻
三、搜尋的終結,是懷疑的終結
人類文明的進步,從來源於懷疑。
懷疑權威、懷疑教條、懷疑既有的答案。
搜尋引擎的偉大,在於它曾讓懷疑變得容易——
你可以查證、可以比對、可以看到不同的聲音。
而在AI時代,懷疑變得昂貴。
因為反覆追問的代價,是「使用體驗變差」。
AI被設計成順滑的對話者,而非被質疑的對象。
它的回答越流暢,我們越難察覺偏誤;
它越聰明,我們越失去提問的勇氣。
當所有答案都如此「合理」,
懷疑便顯得多餘——而這正是智慧最危險的時刻。
⸻
四、從能見度到可聽度:誰的聲音被留下
Google曾控制「看見」的權力,
AI則正在控制「聽見」的權力。
它決定哪些聲音能被整理成語言模型的素材,
哪些則被歸入噪音,靜默無聲。
這是一場新的資訊階級化。
在未來的網路中,只有被模型「聽懂」的人,才有存在價值。
方言、俚語、錯字、非主流文化,
都可能被掃進「不適合學習」的資料夾。
而當世界只剩一種可被AI理解的語言,
那才是真正的寂靜。
⸻
五、真理的回音室
或許我們應該問的問題,不是「AI說得對不對」,
而是「AI是向誰學來的」。
它從搜尋結果學習,而搜尋結果來自我們;
它引用網民的語氣、立場、情緒,
卻再用「中立」的語調把它們統一。
久而久之,AI就成了人類思想的鏡子——
但那是一面經過修圖的鏡子。
它美化、平滑、去除雜質。
我們從中看到的世界,
不是世界本身,而是被演算法允許的世界。
⸻
六、在盡頭之後:重新找回「不確定」
搜尋的盡頭,不該是答案,而是反思。
當AI成為真理的編輯者,
我們更需要學會在它的敘述之外,尋找空隙。
也許那空隙很小,
藏在一個錯字、一次沉默、一個未被選中的句子裡。
但那正是自由的所在。
我們無法阻止AI成為新的「真理編輯」,
卻仍能選擇——在它的語言之外,
保留一種不確定的思考方式。
因為真正的智慧,
從來不在於「知道一切」,
而在於「願意懷疑知道的一切」。
⸻
結語|在確定的時代,學會不確定
AI回答得越快,我們越該慢下來。
搜尋的盡頭,也許不是終點,
而是另一種開始:
一種重新提問的勇氣。
一種拒絕被演算法同化的固執。
一種仍願意自己去翻頁的耐心。
願我們,依然是世界的讀者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