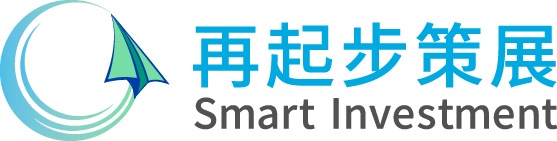創辦人語
除夕在地下書街,重遇啟蒙的名字
相片中見到志文出版社、九歌出版社、爾雅出版社、遠景出版社的名字,這些出版社的作品對我來說是有特別意義的,是「啟蒙」的存在。
除夕那天,我們經過中山地下街。

草菇顯得很開心,也確實很有收穫——不少可愛的 IP 周邊,還有各種國際品牌的陳列方式可以細看、比較、偷師。他終於買到自己喜歡的電腦袋,也成功抽到心儀的盲盒。
那是一個讓人願意慢下來、願意逗留的地方。
我也非常喜歡這個地方。
那裡附近,有書街。
在中山地下書街的一個角落,我看見一個小小的專門擺設,並排放着這幾間出版社的書。
那一刻,某些非常久遠、卻一直沒有消失的記憶,忽然浮了上來。
我其實不知道為什麼,自己對台灣最有感情的書店,始終是第一代的 誠品書店敦南店——那家二十四小時、在敦化南路的誠品。
那時候我多半是出差來台灣。白天有工作,真正屬於自己的時間,總是在夜裡。
三十多歲,精神仍然旺盛,常常在書店裡流連到凌晨三、四點,然後走到復興南路,吃一碗清粥小菜。
看書、清粥。
這種組合,不是其他城市可以提供的。

如果說「最喜歡逛書店的地方」,其實還要再往前推——九十年代的重慶南路。那時候,整條街應該有超過一百間書店。
我最早接觸台灣書的,其實是在香港的二樓書店,大概是八十年代末開始。
只是今天,在地下書街看到那個角落,那幾個出版社的名字同時出現,讓我意識到:原來它們,一直站在我閱讀世界的入口。
作為一個香港教育制度的產物,我算是很早開始看課外書的那一類學生。
非常幸運,大概小學四年級,班主任要求每個學生出十元左右,大家一起買一些課外書,在課室設一個「圖書角」。我也是從那時候,第一次知道什麼叫做「叢書」。
多半是故事、人物傳記,還有一些經典的簡化版本——《三國演義》之類。我在小學時看完這些,竟然會跑去圖書館找完整版,先看白話文,再不自量力地挑戰文言文。看不懂的,就去問老師。
老師大概沒想到,他一番好意,會為自己添上一個如此麻煩的「問題學生」。
升上中學後,看課外書的時間比教科書多。讀的多是歷史、武俠小說。反而到中三、中四開始,因為晚上在工廠工作,有好幾年幾乎沒有再認真讀過什麼課外書。
直到 1989 年,上了大學。
那是真正的開眼界。
在中文大學,通識教育被非常認真地對待。雖然我主修數學,但一個學期讀六、七科,真正是數學的,只有三科。其餘的,是哲學、歷史、電影、心理學、社會學。
那種感覺,有點像長期處於饑荒狀態的人,忽然站在一張擺滿食物的桌前。

也正是從那時候開始,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識到:世界,原來這麼大。
那幾年,旺角的田園書店,是我幾乎每個星期都會去的地方。而我在那裡看到最多的,正正就是 志文出版社、爾雅出版社、遠景出版社、九歌出版社 的書。
其中,又以志文讀得最多。
因為那時候,我大量地讀哲學,還有各種思潮的書。大學一年級,我幾乎是全情投入存在主義——這些出版社,既出版哲學家的故事,也出版原著的中文翻譯,同時還有存在主義文學作品。
回頭看,那應該正是我離開武俠小說、歷史小說與通俗歷史書之後,第一次真正被推進一個更寬闊閱讀世界的起點。

所以,在 2025 年的最後一天,在地下書街再一次看到它們,心裡其實是溫馨的。
不是因為懷舊本身,而是忽然明白:有些書、有些出版社,真的陪人走過了很長的一段路。它們不喧嘩、不張揚,卻默默站在某些人的成長線上,等你有一天回頭,才發現自己曾經從那裡出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