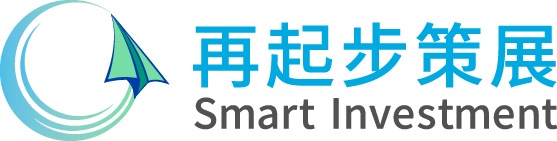《存酒人》:在微醺與留白之間,練習告別
(沒有劇透的視評)
港劇越來越多流水線式的敘事,ViuTV 的新劇《存酒人》(Before The End),卻是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例外,可以脫離這種模式。
作為一部改編自香港作家海笑同名小說的作品,《存酒人》把螢幕縮在一間即將結業的市井酒吧,但它真正關心的,並不是酒吧會不會倒閉,什麼時候關閉?
而是那些酒客在人生轉彎前後,被悄悄留下來、不只是那些留下來的酒,還有一直未被好好處理的關係。
它不像傳統港劇追逐清晰的起承轉合,而更像一種低度醉意中慢慢浮現的情緒體驗——正如人生本身,我們很少等到「準備好了」才告別。
許多重要的東西,往往是在沒有預視之下,就這樣淡出了生活,只留下幾處空白,和一點難以言說的哀愁。

酒吧是城市的情感容器
《存酒人》職場地設定容易,令人想起《深夜食堂》相比,但兩者的設定其實南轅北轍。
《深夜食堂》相信「被理解就能被治癒」,所以很多類似心理治療的敍事交代,把每一個食客的故事講得非常清楚;
《存酒人》卻不急於撫平任何情緒。
它沒有為角色安排出口,也沒有替觀眾準備答案。
十四支寄存在吧台、卻久久未被領走的存酒,成為整部劇的敘事起點。
每一支酒,都是一段未竟的關係、一個無法回收的時刻。
它們被妥善保存,卻都是早已錯過最合適被打開的時間。
單元劇的結構,讓人生像被切成一塊塊斷片:
一段曖昧卻無法兌現的舊情、一場磨蝕多年的婚姻、一群表面和樂、內裡各自沉默的老朋友。
這些都是我們人生的寫照。
這些故事彼此獨立,卻在情感層次上互相呼應,慢慢拼湊出人與人之間那些「未完」與「未說出口」的部分。
正如現實生活裡,多數關係並不是轟轟烈烈地結束,而是在一段對話之後、一杯酒之後、一個背影轉身之後,靜靜散場,沒有道別,便不再相見,
微觀視角與留白的美學
《存酒人》最動人的地方,不在於戲劇衝突,而在於它對日常情感的高度尊重。
鏡頭語言克制,配樂節奏節省,角色之間的沉默並非空白,而像一種有意識的停頓。它拒絕把所有情緒說清楚,而是把空間交還給觀眾——讓我們自行思考:這段關係為何走到這裡?
那個人,為什麼選擇在那重要一刻沉默?
留在杯底的,不只是酒。
存酒的人,帶走的往往只是酒,卻把更多無法帶走的東西,留在原地。
首集《爵士之夜》正是最典型的例子。女主角喝完最後一杯酒,沒有回頭,也沒有解釋,只是轉身離開。鏡頭不追逐情緒,不為這段關係下結論,而是讓「放下了卻未必釋懷」的狀態自然存在。
這種「點到即止」,不是敘事技巧,而是一種對人生未完成狀態的直視。
《存酒人》的表演方式,與它的敘事美學高度一致。
邱傲然(Tiger)、楊樂文(Lokman)等人的演出,不追求情緒爆發,而更像是在生活裡慢慢滲出的反應。情感不是被「演」出來的,而是在對話的縫隙、動作的遲疑、眼神的停留中浮現。
這種表演,與劇本刻意留下的情感空白形成共振——不急於填滿,不刻意放大,而是讓行為與沉默本身成為語言。
第四集《一場朋友》透過彭秀慧、凌文龍等人的聚會,層層剝開朋友之間的虛偽與秘密。
第七集《紙婚乾邑》中余香凝與梁仲恆飾演的夫妻,透過對話道盡婚姻中的磨擦;超市、後巷、的士裡的長鏡頭,在場面調度中完全感受到戲劇張力。
第十四集,董瑋飾演患腦退化症的退休特技人,與談善言飾演的女兒之間的故事。
他們的故事沒有結局,他們的生活仍然在繼續,只是有些感覺已經淡忘、消逝。
《存酒人》帶着非常強烈而自覺的電影質感。
導演並非單純拍劇,而是把不同電影類型的語言,滲入各個單元之中。選酒與美術設計的細緻程度,在近年的港劇中實屬罕見。
每一支酒,都像一個被封存的時間標本,提醒觀眾:這些故事重要的,從來不是結局,而是它們曾經存在過。
我們年少時聽故事,總愛追問「最後主角怎麼樣」;長大以後才明白,結局往往不是最重要的部分。
在告別的年代,這是一部剛剛好的作品
在香港影視工業轉型、創作資源緊縮的當下,《存酒人》並非一部聲勢浩大的作品。它更像一杯慢慢釀成的威士忌——入口時有一點刺痛,卻在回甘時留下溫度。
它提醒我們,港劇仍然可以不靠誇張設定、不靠情節推進,而是透過細膩而誠實的情感,回到人與人之間最真實的狀態。
而這,或許正好對應著香港此刻的處境。
我們正身處一個告別的年代。
告別熟悉的街景、熟悉的節奏、熟悉的關係。
很多離開,都沒有預告;很多失去,都來不及整理。
這種感覺幾乎人人都有,卻很難被清楚說出口。
《存酒人》沒有替我們解釋這個時代,卻替我們保存了那種情緒。
它的英文片名其實更加點題——Before the End。
在完結的前夕,我們真的就可以釋懷、真的能夠放下嗎?
或許不能。
但至少,在微醺與留白之間,我們學會了先與失去共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