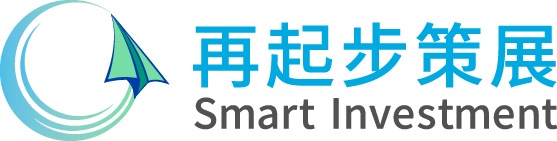草菇日語教室
如何聽懂自動詞/文: So Mei
2019 年。
那一年,香港的空氣很重。
我和草菇老師,是因為一張在網路上合作的製造海報而第一次認識的——那是一張勸喻香港年輕人不要自殺的作品。
不是什麼輕鬆的開始,而是一個必須非常小心用字、非常克制情緒的時刻。
後來,很久之後,大半年之後,我才知道,草菇是日語老師,而且還是我任讀的日語學校裡、另一個班的老師。
在香港,我前後讀過三間日語學校,主要是在香港大學海外進修學院,以及香港日本文化協會。原來草菇老師,一直是這兩間學府裡相當有名的老師。
2020 年下半年,我正好讀到 N4 裡最容易卡關的一章:他動詞與自動詞。
我記得我私下請教他,問了一個其實一點也不像文法問題的問題——
「為什麼日本人那麼喜歡把人藏起來?」
他沒有急著講規則,只是用一張插圖慢慢解釋:
不是誰做了什麼,而是事情變成了什麼樣子。
杯子碎了。
門關上了。
燈亮了。
事情發生了,但主詞不一定要站出來。
五年多過去了。今天在草菇日語的課堂上,我又一次見到這張圖。
如果老實說,我並不覺得自己當時就「懂了」。
那個概念比較像是一顆被放進心裡的種子,沒有立刻發芽,只是在不同的人生階段,偶爾被觸碰一下。
直到這兩年。
草菇日語學校有很多課程我都有參與,其中最特別的,是星期一晚的網上課程。這是草菇日語學校在台灣開設的第一個課程,從 2024 年 1 月 15 日開始,不知不覺,已經走了兩年。
我很喜歡和這一班同學一起學習的感覺。
我從來不是一個過分謙虛的人,但我的語文能力的確比較弱。小時候就被學校評為有語言障礙,發音和聆聽都不成;於是我逼自己多閱讀,用另一種方式,慢慢走出一條路。
2019 年,在人生最迷惘的時候,我幾乎是帶著一點自我懲罰的心態,斷斷續續地開始學日語。
後來來到台灣,重新從頭再來。2024 年 1 月 15 日開始的這一班,我們真的從五十音開始,由零開始,一步一步往前走。
沒有誰比較快,也沒有誰被催促。
每個人,都在自己的節奏裡。
這一班同學,是我見過最有學習熱誠的一班人。大家都很忙,卻沒有人放棄。大家不追進度,反而希望老師慢慢講清楚。那種「不急著完成,而是想真正學懂」的氣氛,本身就很難得。
我也很放肆地在班中表演我走調的發音
今天,我們一起學到《大家的日本語》第 29 課與第 30 課。

這一次,自動詞與他動詞,第一次不再只是文法分類,而像是一扇文化的窗,被慢慢推開。
在中文世界裡,我們習慣用「誰做了什麼」來理解世界。句子的重心,往往落在行為者身上:
「我打破了杯子。」
「他關上了門。」
動作與責任是連在一起的,語言自然把「主體」推到最前面。
但日文的自動詞,卻常常把視線移開了「誰」,轉而凝視「事情本身的發生」。
杯子碎了(コップが割れた)。
門關上了(ドアが閉まった)。
事情就這樣發生了。
好像不是誰「做了」,而是世界在某個時刻,「變成了這樣」。
這種語感,對習慣中文思維的學習者來說,非常困難。
不是因為記不住動詞,而是因為它要求我們放下那種「一定要交代清楚主詞」的衝動。
學習自動詞,其實是在練習一種退後半步的觀看方式——
不急著追究責任,不先指認主角,而是先描述狀態。
第 30 課,會把這種差異進一步放大。
「予定が決まりました。」
「準備ができました。」
聽起來像是事情「自己」完成了。
這不是逃避責任,而是一種刻意把人放在背景裡的表達方式。
也正是在這裡,我突然明白,為什麼日本的文學、日本的電影,常常讓人感到一種抽離。
它們很少緊貼某一個強烈的主觀視角,而是慢慢描寫天氣的變化、空間的移動、時間的流逝、關係的位移。人物彷彿只是站在世界裡,看事情一件一件發生。
那種視覺與敘事的抽離,本身就是一種「自動詞的視角」。
這正是許多日本文化的縮影。
在日本,事情往往比個人重要,流程比情緒優先,狀態比動機先被說出口。語言反映了一種世界觀:人本來就不是,無時無刻都站在舞台中央的主角,而是與環境、時機、他人,共同構成情境的一部分。
回頭看,其實世界一直都變得很快。
很多事情,事後我們根本很難找到真正的第一因。
也許,學習這種抽離、保持距離的觀看方式,本身就是一種對我們有益的智慧——
不是什麼都要立刻下判斷,不是每件事都非得找出一個「誰」。
對學習者而言,最大的困難,從來不只是「這個動詞要不要用を」,而是要接受一件事:
有些語言,不是用來強調「我做了什麼」,
而是用來說明——「現在,是什麼樣子」。
也因此,當我今天在課堂上,再一次自然地說出
「壊れています」、「始まりました」,
心裡浮現的,並不是發音終於過關的成就感,而是一種很熟悉的感覺。
原來,這六年來,我一直都在慢慢理解這件事。
我不是在學一組動詞,
而是在學習一種與世界保持距離的方式——
更含蓄、更留白,也更容許事情在沒有主角的情況下,被溫柔地說出來。
這或許正是日文自動詞最難、也最迷人的地方。